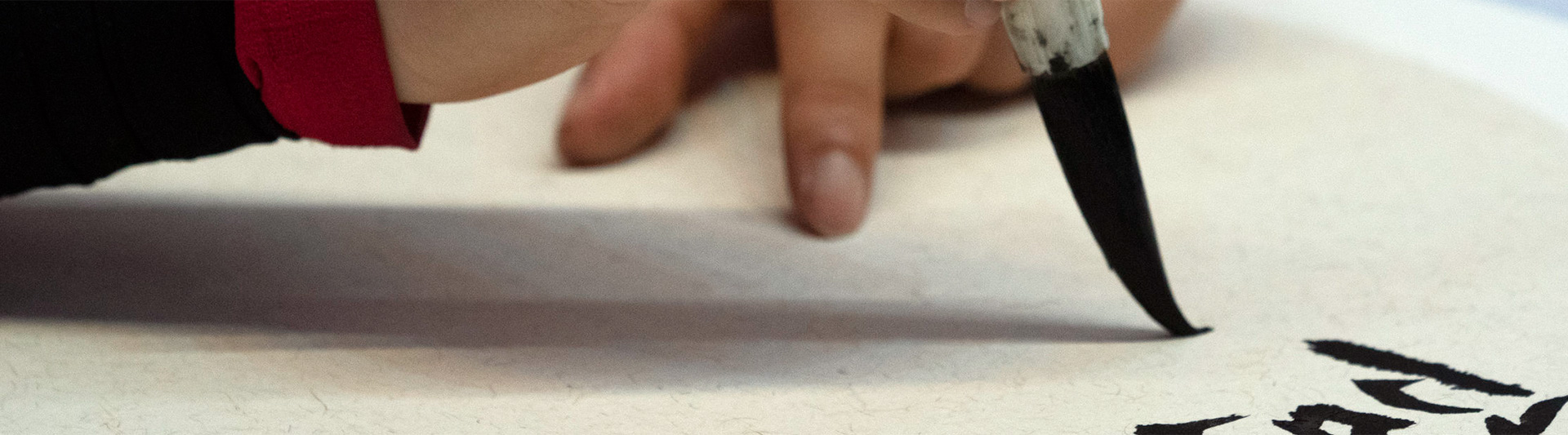-
-

- 2019-04-12 协会动态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漫游指南
1972年,出于对自然与人居环境急速变化的反思和应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这一公约成为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最成功的公约之一,已有近200个国家加入,接近奥运会的规模。也和现代奥运会一样,它既有着强烈的民族国家属性,又以更古老的普世价值和全人类的和平与共同进步为根本。世界遗产综合之前西方遗产保护运动的思辨成果,从无到有建立了一套有着极强操作性和全球适应性的遗产认定和保护管理体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31年,40个文化遗产列入,中国在加入、学习、贡献、发展世界遗产实践的过程中,无疑也在增强对自身遗产和文化的认知。而这些在国际舞台上隆重登场的杰出遗产也在从各个角度讲述那个永远讲不完的中国故事。这些遗产如此丰富,时空跨度辽阔,每一处都明星一样耀眼,我们在用国际通用的语言将它们介绍给世界之时,或许并不会同样关注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它们是否构成一幅整体图景。或者是否这一图景已经碎片化,像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没有能够在现代语言中找到一个完整的表达。这也是我们设计这套系列纪念品思考的起点,用一条最简单的线代表那些无形又强大的力量,承载变化也贯穿始终。这条迂回曲折、延绵不断的线,就像是江中渔夫的鱼线,抛向天地,看时间蜿蜒流转,看淡历史,也看着历史成为我们每个人。而这个世界遗产的旅程并无始终,可以从任何一点开始,即使是碎片,窥见的或许都是一整个中国。这也是一个私人的旅程,带上我们为您准备的小包裹,里面有最简单的地图、尺子、笔记本… 去发现,发明最恰当的语言,讲述你自己的中国,我们所有人的中国。书: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之旅笔记本页:您可以制作自己专属的世界遗产旅行手账月历:金属尺:丝路连接东西,运河贯通南北便签(2本):看似坚固的 也很脆弱易逝书签:环保包装袋:正反信息框:本套纪念品为限量版,将发送给协会的国际个人会员和已缴费的团体会员单位,请注意查收。如有其他人感兴趣,可发送邮件至协会邮箱(icomoschina@icomoschina.org.cn)联系购买,我们将以成本价出售,个人会员(含国内、国际会员)享受8折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
-
- 2019-04-12 会员动态
团体会员入会名单
经协会审核通过,2019年第一批团体会员名单如下(共39家,排名不分先后) 单位名称 郑州市文物局 浙江省临海市古建筑工程公司 河南中智方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云南建川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营造院文物保护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景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夏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故宫古建筑有限公司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系(吉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广东观道文物古迹更新活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江门市川川古建筑文化遗产研究院 广东侨乡建筑修缮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粤秀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广东南秀古建筑石雕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南越历史建筑保护设计监理有限公司 广东思成园林建筑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欧阳川传统建筑营造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南粤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泉州市刺桐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国信司南(北京)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少匠古建园林营造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磊古建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曲阜市华厦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安徽徽博古建园林有限公司 安徽徽博文物修复研究所有限公司 厦门惠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德弘园林古建筑有限公司 临海市广顺源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北县元中都遗址保护区管理处 广州市建筑遗产保护协会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 曲阜市义德古建艺术有限公司 福建腾飞园林古建筑有限公司 辽宁有色勘察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筑葏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宜兴市金陵文物保护研究所
-
-
- 2019-04-12 会员动态
个人会员入会名单
经协会审核通过,2019年第一批个人会员名单如下(共86人,排名不分先后) 姓名 工作单位 马庆凯 浙江大学 张煜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 杨红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 罗丞涵 故宫博物院 周红萍 澳门文化局文化遗产厅研究及计划处 李伟得 海事及水务局海事博物馆 刘珊珊 北京交通大学 薛皎 陕西省西咸新区西安昆明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李皓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 梁中荟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 刘显超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 刘翔宇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 吕文杰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 刘龙 伪满皇宫博物院科研中心 杨宇 伪满皇宫博物院 赵继敏 伪满皇宫博物院 胡海龙 伪满皇宫博物院 王志强 伪满皇宫博物院 周波 伪满皇宫博物院 傅舒兰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史长存 北京万兴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王思渝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刘弘涛 西南交通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 李南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建筑科创中心 邹兴华 香港特区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 潘玥 《建筑遗产》编辑部 任伟 郑州市文物局 张贺君 郑州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 谭朝洪 北京建筑大学 叶祖立 韶关创盛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王海 广州正度数据处理服务有限公司 张岚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 张影 吉林省乾安县文物管理所 陈晖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际工程部 黄雯兰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际工程部 金昭宇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际工程部 刘志娟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际工程部 马跃宁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际工程部 袁濛茜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际工程部 高晨翔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 张正秋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 王芳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 魏兴乐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 周晓晨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保护中心 袁怡雅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 王璐 陕西省古迹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陈海霖 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王玉宝 曲阜市义德古建艺术有限公司 张欣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夏宇佳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孙晓倩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胡红国 古玩\艺术品经营者 刘逸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旅游管理与规划系 肖彦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殷铭 苏州古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丁军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晋 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张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 高子晗 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宋顾薪 北京数字圆明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李薇 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贤如 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协同创新中心 田颖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党安荣 空间信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清华大学) 周文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清华大学) 吴冠秋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刘斌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田福 山东德弘园林古建筑有限公司 夏生平 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 张剑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杨晓飞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王之纲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 陈兴华 灵渠申遗办公室价值研究组 陈晨 金山区博物馆 刘志明 河北友高律师事务所 田阳 华北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陈云华 浙江省老龄产业协会 梁冰 北京数字圆明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朴文子 北京数字圆明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杨思 北京数字圆明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赵建南 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 孙佳 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 徐斌 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 徐萍萍 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协同创新中心 王心源 UNESCO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 石鼎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
-
- 2019-04-12 资质资格
关于开具2019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报名费发票的说明
各有关单位或个人:2019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报名费发票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统一开具,发票形式为电子发票。在考试结束后2个月内发至单位(如一个单位有多人报考,可将报名费归并统一开具一张发票)或个人邮箱。需要开具发票的单位或个人,请填写《开票信息填写表》,并于2019年5月31日之前发至电子邮箱:zizhi@icomoschina.org.cn 过期将不受理发票开具业务。请确定好报考科目后再开发票,发票一旦开具将不再受理……
-
-
- 2019-04-11 4·18国际古迹遗址日
4·18国际古迹遗址日 ‖ ICOMOS CHINA在清华大学等你
“国际古迹遗址日”又要来啦!今年的4月18日,国际古迹遗址日主场活动在清华大学举办,就让小编来为您介绍一下吧时间:2019 年4 月18日(全天)地点:清华大学设计中心(伍舜德楼)二层绿色报告厅主办方: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上午 全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推介仪式受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开展全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推介活动,通过推介活动,评选出优秀且有示范意义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向社会展示近年来的优秀案例成果。4月18日上午,我们将为大家揭晓今年的优秀项目,并请专业人员为大家介绍项目的经验和思考,以期待促进行业经验交流,引领文物保护行业健康发展。• 下午 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沙龙——多元视野下的乡村景观为配合将于2019年10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ICOMOS年度科学研讨会“乡村遗产”的主题,今年的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定为“乡村景观”(rural landscapes)。4月18日下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将举办“多元视野中的乡村景观”沙龙,邀请文物、建筑、农业、旅游、互联网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向大家讲述他们各自眼中的乡村景观。我们认为,乡村景观,不仅是文化遗产领域的课题,更是涉及多个行业、需要多重视角去共同关照的议题。只有多元的声音、多样的视野,才能给乡村景观一个更加完整的叙事,才能给它的保护和传承更加客观、理性的路径。小贴士:本次活动无需提前预约报名,别忘了携带本人身份证哦~不能亲临现场的朋友们,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也为您准备了全程在线直播,直播方式稍后奉上~感谢文博在线平台、古猫文化科技、大地风景等机构为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
-
- 2019-04-04 资质资格
2019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常见问题及解答
2019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即将启动,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为您一一解答。问题1:本次考试的背景是什么?2017年,文物保护工程从业资格已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为做好文物保护工程资格考核工作,促进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根据《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试行),在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下,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开展本次考试。问题2:什么人可以报名参加本次考试?凡中国公民(含港澳台居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符合《2019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实施细则》第二条“报名条件”中任一一项者,皆可报名。问题3:报名资格是否需要经过审查?考试实行告知承诺制,考试报名时不对报名资格进行审核。报考人员在报名时须本人亲自填报相关信息,并对填报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以及本人符合考试报名条件作出承诺,承担不实承诺的后果。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在审核业绩证明材料和办理专业资格证书时将对报名资格进行审查。问题4:报名是否需要对工作单位有要求?本次考试为个人报名,原则上不需要经过单位推荐,对所属单位的性质和文物保护工程资质不作限定。问题5:在校学生能否报名?如果报考人员为在校学生,但已经具备报名条件中相关学位/学历,以及从事文物相关工作年限的要求,可以报名。全日制教育的年限不计入工作年限,非全日制教育可计入工作年限。问题6:考试通过标准是什么?各科考试成绩达到试卷总分的60%即为通过(或合格)。责任设计师和责任工程师专业应试人员在连续5个年度内通过公共必考科目、本专业的专业必考科目及至少1个本专业专业选考科目后,责任监理师在连续5个年度内通过公共必考科目和2个本专业的专业必考科目后,即视为通过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问题7:什么叫“连读5个年度”?考试有效期5个年度指的是什么?考试实施5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如考生2019年参加考试,其需要在2023年内(2023年为2019年起的连续第5个年度)取得该专业类别通过所需全部科目的合格成绩。2015年的成绩在2020年不再有效,同理,2019年的成绩在2024年不再有效。如考生甲在2019年度考试中通过了责任设计师的公共必考科目和专业必考科目,但没有通过专业选考科目,则应在2023年内(2023年为2019年起连续第5个年度)内通过专业选考科目。问题8:考试通过后如何领取证书?文物保护工程资格考核工作,包含资格考试和业绩审核两个环节,考生通过考试后,须在5个年度内提交考试成绩证明、人员信息证明材料、业绩审核证明材料并经审核通过,方可获得相应专业资格证书。举例:如应试人员在2019年考试成绩合格,可在成绩合格后的第5个年度(2023年)年底前申领资格证书;如逾期未申领资格证书,则需再次参加考试。问题9:2015年的考核成绩是否有效?参加2015年度考核并取得专业资格证书者,本次考试可增报本专业其他专业选考科目,免试公共必考科目和本专业必考科目;参加2015年度考核并取得专业资格证书者,如报考其他专业类别(如2015年参加责任设计师考核并领证,2019年要参加责任工程师考试),则需参加该专业类别的公共必考科目和专业必考科目。参加2015年度考核,但尚未获得专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其2015年度取得的考试科目合格成绩在2019年度(2019年为连续的第5个年度)仍然有效。但因本次考试必考科目发生变化,如在2015年度考试中未同时通过“文物保护法规和行业准则”和“勘察设计和规划通论”(或“施工通论”),本次考试须同时报考公共必考科目和对应专业类别专业必考科目。问题10:已经有证书的可以增报其他科目吗?已经取得相应专业资格证书且各科目的合格成绩在有效期(5个年度)内的,可增报本专业其他专业选考科目,免试公共必考科目和本专业必考科目;已经取得相应专业资格证书且有公共必考科目或专业必考科目的合格成绩超出有效期(5个年度)的,增报本专业其他专业选考科目时,合格成绩超出有效期(5个年度)的公共必考科目或专业必考科目须重新报考。问题11:本次考试专业类别有哪些?考试设责任设计师、责任工程师、责任监理师3个专业类别。其中,责任设计师和责任工程师,设公共必考科目、专业必考科目、专业选考科目;责任监理师专业类别设公共必考科目和专业必考科目,不设专业选考科目。问题12:能否跨专业类别报考?在一次考试中,报名人员只能选择责任设计师、责任工程师、责任监理师三个专业类别中一类报考,不得跨专业报考。如果已经具有某一类别专业资格证书,可以选择其他专业类别之一报考。问题13:本次考试是否有大纲,是否组织培训?本次考试大纲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官方网站发布(www.icomoschina.org.cn),考试大纲中列出考生所需的参考书目,本次考前不组织培训。问题14:考试地点选择有限制吗?没有限制,考生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考试城市,并由当地考务组织机构安排考试地点。北京居民也可以选择西安或南京作为考试地点。问题15:报名费收取依据是什么?本考试费为经营服务性收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命题、考务组织等方面工作成本进行测算,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不从中盈利。问题16:报名费发票如何开具报考人员若需开具考试费发票,请在缴费完成后关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官方网站稍后发布的有关通知。问题17:多久能出成绩?两个月内公布考试成绩,成绩将在中国人事考试网发布。问题18:准考证什么时候发放?考试时具体要求是什么?报名缴费成功后,请根据“报名须知”里要求的相关事项准备参加考试各项手续,如有关于考试要求等具体问题,建议考生直接咨询当地考试中心。问题19:下一次考试是什么时候?原则上每年举办一次考试……
-
-
- 2019-04-04 资质资格
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大纲
各位考生, 由于在大纲发布时,已有部分规范更新并实施,为方便考生进行复习特此更新。更新部分主要涉及保护规划科目的《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 50298-1999、《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 50357-2005更新为了《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GB/T 50298-2018、《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标准》GB/T 51294-2018、《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 50357-2018,特此通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下载地址: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大纲……
-
-
- 2019-04-03 资质资格
关于开展2019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
关于开展2019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为促进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健康发展,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根据《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试行)和《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等有关规定,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负责组织开展2019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报考资格:凡中国公民(含港澳台居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且符合本考试报名条件的,均可报名参加考试。二、考试时间:2019年6月22日、23日。三、考试地点:本次考试在北京、西安、南京三个城市设考点,报考人员可自行选择考试城市。考试详细地址以准考证标注为准。四、考试内容:考试科目包括公共必考科目、专业必考科目、专业选考科目。详细内容参考《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大纲》(附件1)。五、报名方式:2019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采用网上报名、网上缴费的方式。三地考试机构将自4月5日起陆续开放报名,至4月20日截止,请大家密切关注中国人事考试网(www.cpta.com.cn)关于考试报名有关事项的信息,在中国人事考试网填写并提交报名信息,上传照片,并按规定完成网上缴费(为保证报名顺畅,推荐使用IE7以上版本浏览器)。2019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实行告知承诺制,考试报名时不对报名资格进行审核。报考人员在报名时须本人亲自填报相关信息,并对填报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以及本人符合考试报名条件作出承诺,承担不实承诺的后果。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在审核业绩证明材料和办理专业资格证书时将对报名资格进行审查。报考人员只可选择责任设计师、责任工程师、责任监理师三个专业类别其中一类报考。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费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收取,收费标准为135元/人˙科。报考人员若需开具考试费发票,请在缴费完成后关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官方网站有关通知。六、其他事项:已取得专业资格证书的应试人员,本次考试可免考公共必考科目和本专业的专业必考科目。参加2015年度考试,尚未获得专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其2015年度考试取得的考试科目合格成绩在2019年度仍然有效。本次考试具体报名条件、考试科目介绍、考试要求和证书发放等相关事宜详见《2019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实施细则》(附件2)。附件:附件1.1-《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大纲》word版附件1.2-《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大纲》pdf版附件2-《2019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实施细则》联系人:孙滢、张畅、燕海鸣联系电话:010-84633309、84156597,13263446893电子邮箱:zizhi@icomoschina.org.cn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2019年4月3日……
-
-
- 2019-04-03 资质资格
2019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实施细则
为做好文物保护工程资格考核工作,促进文物保护工程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根据《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试行)和《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制定本细则。一、组织机构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负责文物保护工程资格考核工作,考务工作委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二、报名条件凡中国公民(含港澳台居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均可申请参加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以下简称“考试”):(一)取得相关专业的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同等学历,并从事文物相关工作4年以上的;(二)取得相近专业的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同等学历,并从事文物相关工作5年以上的;(三)取得其他专业的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同等学历,或相关专业的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并从事文物相关工作6年以上的;(四)取得相近专业的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并从事文物相关工作7年以上的;(五)取得其他专业的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并从事文物相关工作8年以上的;(六)具有相关专业的大专及以下学历,并从事文物相关工作8年以上的;(七)具有相近专业的大专及以下学历,并从事文物相关工作9年以上的;(八)具有其他专业的大专及以下学历,并从事文物相关工作10年以上的。报名条件中的工作年限,是指取得申报学历(或同等学位)前后在文物保护行业的累计工作年限,按周年计算,计算截止日期为报考年度的12月31日。其中,全日制教育的年限不计入工作年限,非全日制教育可计入工作年限。报名条件中的专业相关性,包括“相关专业”“相近专业”“其他专业”等,具体界定见下表:专业相关性对照表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同等学历,须参照《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须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大专学历须参照《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大专以下学历须参照《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各学历(或同等学位)目录在查询时应对应其各自专业目录,不同学历(或同等学位)之间不得跨目录申报。由于教育部发布的各专业目录存在名称调整与更新情况,且各高校具有自主设置专业的情况,因此,专业相关性对照表难以覆盖所有专业名称。专业名称不在专业相关性对照表内,若主干课程设置及学时与相关专业一致,可按“相关专业”报考,若多数主干课程设置及学时与相关专业一致,可按“相近专业”报考。三、考试设置和报考规则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考试设责任设计师、责任工程师、责任监理师3个专业类别,报考人员只可选择其中1个专业类别报考,不可跨类别报考。各专业类别考试科目设置见下表。各专业类别考试科目设置报考责任设计师或责任工程师专业的人员,须在连续5个年度内通过公共必考科目、本专业的专业必考科目及至少1个本专业专业选考科目(2023年为2019年起连续第5个年度),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业绩审核方可取得专业资格证书;已取得专业资格证书的应试人员,可免考公共必考科目和本专业的专业必考科目。报考责任监理师专业的人员,须在连续5个年度内通过公共必考科目和2个本专业的专业必考科目,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业绩审核方可取得专业资格证书。四、报名方法2019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采用网上报名、网上缴费的方式。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可在规定时间内在中国人事考试网(www.cpta.com.cn)注册、报名及缴费。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费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收取,收费标准为135元/人˙科。报考人员若需开具考试费发票,请在缴费完成后关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官方网站有关通知。2019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实行告知承诺制,考试报名时不对报名资格进行审核。报考人员在报名时须本人亲自填报相关信息,并对填报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以及本人符合考试报名条件作出承诺,承担不实承诺的后果。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在审核业绩证明材料和办理专业资格证书时将对报名资格进行审查。五、考试时间、地点2019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于2019年6月22日、23日举行,在北京市、江苏省(南京市)、西安市三地设置考点,报考人员可自行选择考点城市。各考点详细地址以准考证标注为准。本次考试为闭卷考试,各个科目的考试时间均90分钟,试题均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考生应试时,应携带黑色水笔、2B铅笔、橡皮。各科目考试时间安排如下:6月22日8:30—10:00 法律法规与工程管理11:00—12:30勘察设计通论、施工通论、监理通论14:30—16:00古建筑(设计师)、古建筑(工程师)、监理实务17:00—18:30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设计师)、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工程师)6月23日8:30—10:00古遗址古墓葬(设计师)、古遗址古墓葬(工程师)11:00—12:30石窟寺及石刻(设计师)、石窟寺及石刻(工程师)14:30—16:00 壁画(设计师)、壁画(工程师)17:00—18:30 保护规划(设计师)六、专业资格证书的获取获取文物保护工程专业资格证书的条件是通过考试并通过业绩证明材料的审核。1、考试成绩通过规则各科考试成绩达到试卷总分的60%即为通过(或合格)。责任设计师和责任工程师专业应试人员在连续5个年度内通过公共必考科目、本专业的专业必考科目及至少1个本专业专业选考科目后,责任监理师在连续5个年度内通过公共必考科目和2个本专业的专业必考科目后,须在考试通过日起5个年度内,提交考试成绩证明、人员信息证明材料、业绩审核证明材料并经审核通过,方可获得相应专业资格证书。如应试人员在2019年内考试成绩合格,可在2023年年底前申领资格证书。已经取得相应专业资格证书且各科目的合格成绩在有效期(5个年度)内的,可增报本专业其他专业选考科目,免试公共必考科目和本专业必考科目;已经取得相应专业资格证书且有公共必考科目或专业必考科目的合格成绩超出有效期(5个年度)的,增报本专业其他专业选考科目时,合格成绩超出有效期(5个年度)的公共必考科目或专业必考科目须重新报考。参加2015年度考试,尚未获得专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其2015年度考试取得的考试科目合格成绩在2019年度仍然有效(2019年为连续的第5个年度)。2、业绩认定与通过规则所提交业绩证明材料的项目级别应符合《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试行)要求:(1).责任设计师:主持完成至少二项工程等级为一级,或至少四项工程等级为二级,且通过相应文物主管部门审批的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项目;或者作为主要技术人员参与完成至少四项工程等级为一级,或至少八项工程等级为二级,且通过相应文物主管部门审批的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项目。(2).责任工程师:主持完成至少二项工程等级为一级,或至少四项工程等级为二级,且工程验收合格的文物保护工程施工项目;或者作为主要技术人员参与管理至少四项工程等级为一级,或至少八项工程等级为二级,且工程验收合格的文物保护工程施工项目。(3).责任监理师:主持监理至少二项工程等级为一级,或至少四项工程等级为二级,且工程验收合格的文物保护工程项目;或者作为主要人员参与监理至少四项工程等级为一级,或至少八项工程等级为二级,且工程验收合格的文物保护工程项目。3、人员和业绩证明材料的内容(1).人员信息证明材料:包括单位合同(报考时所填单位与合同单位不一致的,应提供报考单位离职证明),毕业证书及学历证书的复印件及社保证明文件(需盖当地社保部门公章)。(2).业绩审核证明材料勘察设计:包括项目合同、项目批准文件的复印件、单位盖章的证明材料(说明人员在项目中承担的责任和工作内容);施工/监理:包括项目合同、项目批准文件、验收文件的复印件、单位盖章的证明材料(说明人员在项目中承担的责任和工作内容)。七、惩戒措施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31号)执行。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2019年4月3日……
-
搜索SEARCH
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