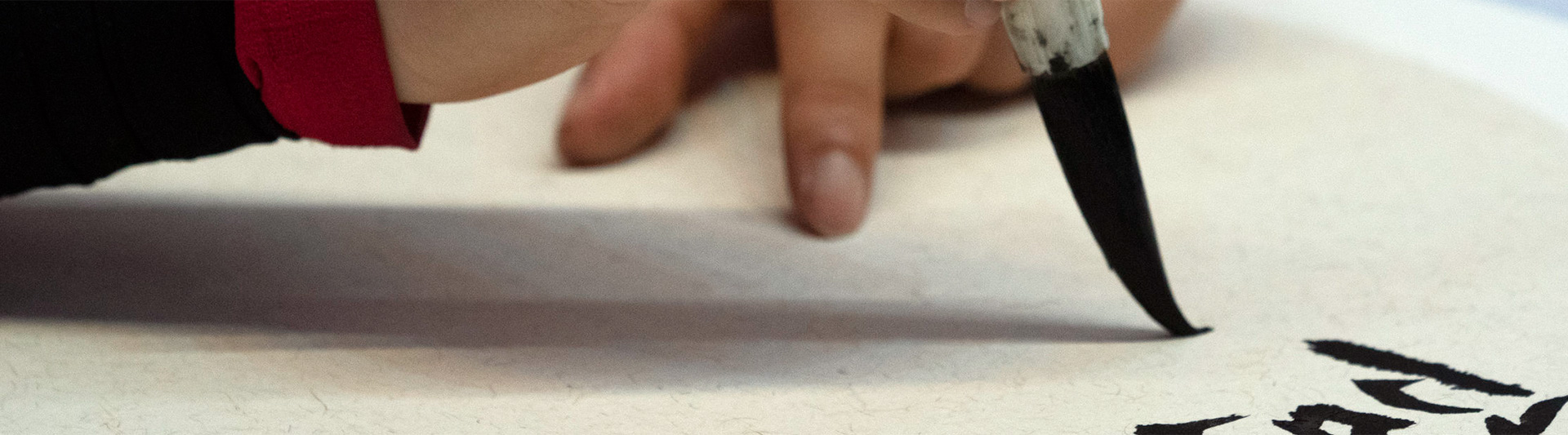ICOMOS发布《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的国际宪章与指南》
2025-03-24
来源: ICOMOS
浏览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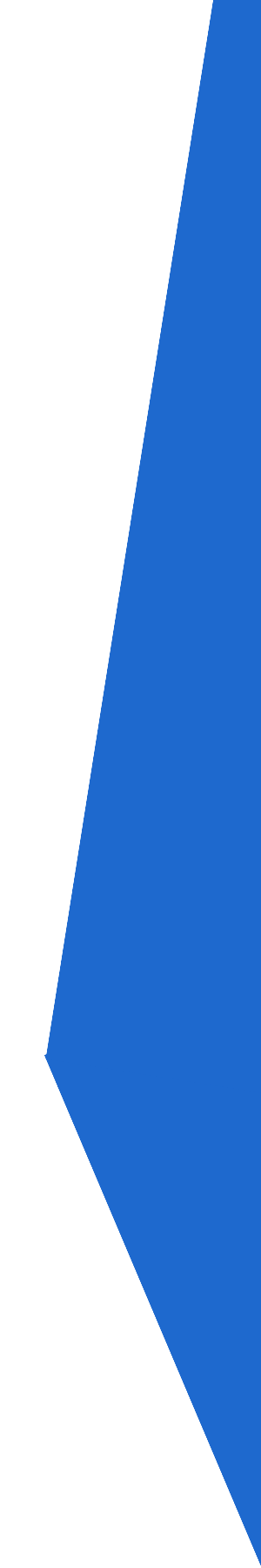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的
国际宪章与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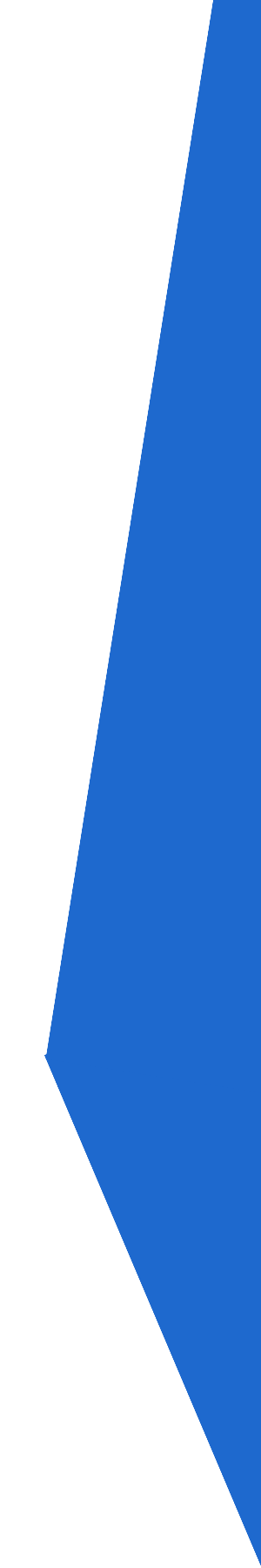
“自由”是指在未受胁迫、恐吓或操纵的情况下,自愿给予同意。自由还指被征求同意的社区在不受外部强加的胁迫、预期或时间安排束缚的情况下自主开展的决策流程。
“事先”指在开发或投资计划早期阶段,在任何授权之前或开始活动之前充分征求同意,而不是在需要获得社区批准时才去征求其同意。
“知情”主要指在征求同意之前,让权利人知晓参与的性质和所提供信息的类型;知情也是持续进行的同意过程的一部分。
“同意”指权利人作出的集体决定,一般通过受影响的土著民族或社区的习惯性决策过程达成。必须根据每个社区独有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行政动态来征求同意,无论他们是否给予同意,都要尊重土著社区的决定。必须让土著民族和当地社区通过自己选择的代表参与同意授予或拒绝的过程,同时尽可能确保青年、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参与其中。
分享到:
最新新闻
-
-

- 2025-11-12 协会动态
【创意交流】长城古堡综合文物与社会调查课题项目会议在京召开
-
-
-

- 2025-11-04 专委会动态
第四届文化遗产防灾减灾年度论坛暨2025年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文化遗产防灾减灾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北京召开
聚焦“充分认识自然灾害风险,提升文化遗产安全韧性”,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文化遗产防灾减灾专业委员会2025年年会于11月1日在北京市成功举办。
-
-
-

- 2025-10-21 总部动态
2025年ICOMOS大会暨科学研讨会召开
2025年10月15日-18日,2025年度ICOMOS科学研讨会在尼泊尔蓝毗尼举行。
-